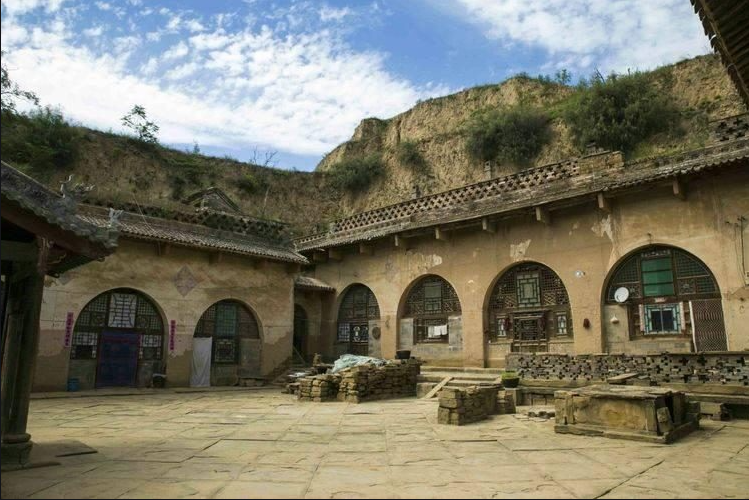
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家有最老的家长活着,不管家中伤了几人,就好像还不曾损失元气似的,因为老人是支持家门的体面的大旗。
六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母亲把爷爷和几个伯父请到了家里,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几个娃娃上学的事情。
母亲作为父亲的遗孀,乡政府每月发七十块钱生活费,几个子女每人每月十块钱生活费。父亲去世已经两年,自从前年小麦遭受冰雹后,山地再也没有耕种,川台地大舅每年帮忙耕种,庄稼地里锄草,秋季收割,都由母亲一个人完成。眼下,二姐已读初三,我读初二,后季四妹就该读初一了。在山庄乡读初中的我们,吃住都在学校,只周六回家一趟。
母亲对爷爷伯父们诉说:“这两年的时间,娃娃吃住在学校,忍饥、忍冻,读书到了紧要关口,是继续读书还是回家务农?我的想法,让她们把初中读完,初三报考小中专,考上了,是公费上学,我可以省点心,以后有一碗饭吃,考不上,只能回家劳动,到了结婚的年龄嫁人。她们的父亲不在了,如果不供她们读书,给她们的父亲不好交代。现在都还小,又是女娃娃,如果回家种地,能耕种还是能锄收?”母亲说完,眼泪汪汪地看着炕上坐着的每个人,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到希望。
这个时候,爷爷开口了:“我现在年龄大了,一天也是吃闲饭的。眼下这世道,自家顾自家都挣得人屁直吼,谁还能顾了别人?自古以来,人分三六九等,肉有五花三层,如果你有啥能耐,就把几个娃娃领出去,人不常说,人挪活,树挪死嘛。”
“我家在齐沟脑,帮着耕种也不方便,顶多是给你帮着锄收一两天。再说,一到春耕春种家家都忙,等人家忙完了,再给你家耕种就晚了,关键是节气不等人,错过了节气,庄稼自然不好。”大伯父语重心长地说。
“我就一个儿子,劳力少,又常年在外,给你帮不上忙。再说,女娃娃念不念书无所谓,迟早是旁人家的一口人,叫回来务农算了。”三伯父是个百里挑一的好车把式,他在门外赶大车,车赶得好,那鞭子能抖出一串花来,十里八里都听得脆响。
“我娃娃多,累受大。实在说哩,我自家也把两条腿伸进一条裤脚里去了。我也是那意思,女娃娃长大了是一门亲,识那么多字有啥用?会写算就行了。”四伯父埋怨道。
爷爷瞪大了眼珠子,盯了四伯父一眼。
“不行啊,我窑里六口子端碗哩,我的大小子还在县高中上学哩。”四伯父脸挺得板平,看着爷爷说。
大伯父用拿烟锅的手揭起帽子,另一只手舒服地搔着五十多岁的夹杂着白头发的光脑袋。三伯父望着他,看他会说什么话,但是他把帽子重新戴上,又擤着鼻涕。也许他擤完鼻涕,会考虑好说什么话吧?但是他又把烟锅插在烟布袋里,慢条斯理地装起烟来考虑着什么,然后从怀里掏出火柴吸烟了……
身躯瘦小的母亲孤零零地站在地上,一霎时内,她还找不到要说的话。
“这事,实在叫我作难。怎么帮你?各家有各家的难处,我这当老人的,实在歪口地说不出来。”爷爷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
此刻,母亲心是凉的,腿是软的,脑袋是木的。她鼻根一酸,眼珠被眼泪罩了起来。但是她咬住嘴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母亲笨拙地掩饰她的窘迫,强装坚强的脸色,冲口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让他们念书,这也是他们父亲的心愿。你们各有各的难处,我能理解,现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了,可我还活着,总不能眼瞅着娃娃们挨饿受冻吧?”
“胡整呢,指头往磨眼里擩,我也不是碟子喝水浅看人,将来这些娃娃考不出去,你再回来?让庄里人看笑谈?”四伯父一句话说出了母亲的顾虑。
母亲接过话茬:“这我都想过,思来想去也没啥,回就回来了,没啥丢人的。得给娃娃们一次念书的机会。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只是把他们领进门。”
太阳挂在西边的天空上,不再那么耀眼,变成了通红一轮,涂在一片片红光闪闪的云层上。村里的炊烟升了起来,在空中扭来扭去。
夜色苍茫中,还没消散尽的炊烟,在村庄上空飘浮着。母亲做了手擀面,爷爷吃了两大碗面,而后含笑地边吸着旱烟,边摸着下巴上一撮被旱烟熏得焦黄的胡须,烟锅还没离嘴,他已打上了盹,倒在炕上。登时鼾声像拉风箱似的,震动得气窗眼中的家雀都患了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