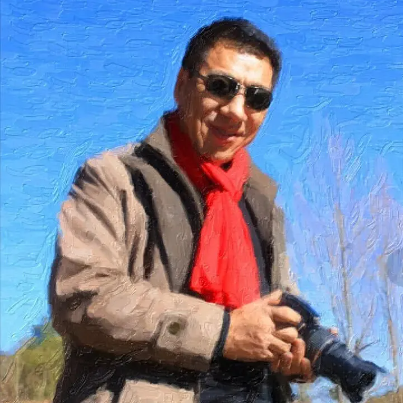
韩超,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致力于散文随笔写作,出版有散文集《蓬窗听雨》《蓬窗望云》《蓬窗啸风》,获庆阳市第六届、第十二届李梦阳文艺奖。曾参与策划创作大型历史文化电视专题片《黄土大塬》,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播出。
在这里聆听庆阳,在这里读懂庆阳。本期的“一点庆阳”,为大家朗诵韩超的散文《匍匐在大地之上》。
匍匐在大地之上
韩超
惊蛰刚过,土地陡然苏醒,整个村庄弥漫着吉祥的气息:牛在大口咀嚼草料,毛驴喷着快乐的响鼻,村道上杂沓着早起的脚步声,以及水桶进入井口的咣当声,风箱煽动的啪嗒声,锅碗瓢盆碰撞的叮当声,孩子尿床被打了屁股后的嚎哭声,声声交错,声声入耳,让村庄的早晨显得吵闹而殷实。
麻雀成群结队,聚在树上、屋檐上吵闹不休,也是在商量今年种什么庄稼吗?麻雀是留鸟,是庄稼人不离不弃的朋友,无论贫穷富贵,它们一年四季都和人一起生息繁衍在村庄里。和狗一样,它们忠实可靠,有时候也发挥着安全预警职能,有陌生人来时,就会“扑棱棱”从地上飞起,聒噪一片,告诉人们来人了。我一直认为,麻雀是村庄里能够透露天意的“神示者”:比如风雨将至,比如庄稼丰歉。

折兴发 摄
新翻过的土地,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散发着泥土芬芳。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大地化腐朽为神奇,不仅完成了自净,而且积聚了巨大能量。前天夜里刚好下过一场透雨,大地湿漉漉的,踩上去松软而柔和,犁铧过处,可以看见已经萌芽的草根,也有一条一条蠕动的蚯蚓。此时此刻,大地像一个待孕的妇人,裸呈着温软的肚腹,毫无羞涩之意,大方而热烈地期待着雨露的滋润与和风的轻拂,风情万种,诱惑着一个叫春天的男人去耕耘、去播弄、去撒下生命的种子。
人哄地一阵子,地哄人一料子。深谷子,浅糜子,荞麦种在浮皮子。父亲一边往地里撒肥料,一边给我讲种庄稼的道理:“这么好的地,不种庄稼干啥?”在父亲这样的庄稼人眼里,土地的命根子,是用来耕种的。农民天生就是种地的命,不种地吃啥?把地撂荒,是一个庄稼人最不能容忍和羞耻的一件事情。长大后,读过一句相同意思的话,蓦然似有所悟:“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土地承包时,曾经饱受饥荒岁月煎熬的父亲主动申请要了许多山地,因为按照亩产划分土地类别,山地可以多分几亩。即便如此,年过花甲的爷爷仍然领着我们把承包山地周边更陡的山洼以及只有羊道的坑坳全部开垦出来,种上洋芋和苜蓿,他说:“洋芋救过人命哩!”陡峭的山坡,沉重的担子,牛皮合成的绳子深深勒进爷爷已经开始萎缩的肩膀,被汗水浸透过无数遍的布褂子在风吹日晒下,浮现出一层深深的黑渍和淡淡的盐白。
爷爷一辈子匍匐在土地上刨食,却一辈子没有过上好日子,饥馑最严重的年代,几乎无力养活奶奶和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爷爷从来没有抱怨过土地带给他一生的负累,只要一脚踏进土地,爷爷就显得兴奋和快乐,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显露出一个地道庄稼人应有的执着劲和道德感。倒是一个从来不沾土地、不种庄稼的人,竟然说了一句貌似很有道理的话:“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当然,他说这话时另有所指,对于爷爷这个一辈子只会务弄土地和庄稼的人,他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敬畏。当然,这是那个年代的人的修养和操守。
爷爷做了一辈子农活,是远近有名的庄稼把式,俗话所说的“扬场左右锨,铡草擩麦秸,耕地豁边边”这些庄稼活里面的把式活,没有一样能难住爷爷。爷爷干农活从来不出蛮力,他会干活,会出力。在我年轻气盛时要一担挑起一百多斤青苜蓿走山路的时候,爷爷及时喝止了我的鲁莽。他像调牛犊和马驹一样,帮我把担子的重量卸到八十多斤:“娃娃家腰腿还嫩着哩,力气没长圆,宁可多跑一趟,不敢贪多出猛力。”
爷爷是在正干活的时候突然跌倒的,从此半个身子不听使唤,整整卧床两年。两年时间的疾病折磨,让爷爷的身体和精神同时松弛以至于坍塌,更多时候他几乎认不得唯一的儿子和两个孙子。生命最后的那个冬日,大爷爷突然来看望久病在床的爷爷。同胞相见,四目相对,竟然能够有一句没一句的交谈半天。大爷爷伏在爷爷耳边大声问道:“你还认得我吗?”爷爷嘿嘿一笑,过了半天竟然叫出了大爷爷的乳名。大爷爷一愣神,随之也嘿嘿一笑,笑着笑着,流下两行浑浊老泪。几日后,爷爷溘然长逝,村里人都说:“庄里最老实的庄稼汉走了!”
转眼过了端午,一夜熏风,川台上的麦子全都黄了,一块一块,高低错落,丰盛厚实,如同盛放在大地上的金子。微风吹过,一缕缕成熟的、芳烈的、新鲜的麦香味道扑面而来,让人迷醉。虽然太阳用最毒辣的光芒炙烤着村庄和大地,可庄稼人谁也不敢有丝毫马虎,或者稍微消停一会儿,都忙着收拾镰刀、绳索、架子车,给碌碡膏油,为牲口加料。“麦黄米黄,秀女下床”,三夏大忙时节,龙口里夺粮,村庄里从老人到小孩,绝对没有一个闲人。

张明政 摄
割麦是很折磨人的活计,身体三折一窝趴在麦地里,热气蒸烤,灰尘蛰蚀,麦芒刷刺,各种折磨叠加在身,实在苦不堪言。一畛地四五百米的麦趟子,仿佛望不到头的漫漫征途,无数次地俯身挥镰,无数次地伸腰擦汗,从搭镰的十犁沟麦子边走边撂,依然赶不到前面去。父亲总是默默地跟在身后,揽下我连跪带爬、丢盔弃甲撂下的那几犁沟麦子,从不站起身展腰或者中途休息。父亲说:“割麦的时候不敢站起来展腰,展一次就想无数次站起来展腰,麦子就把人绊住走不到前头去了!”
碾场是夏日村庄里最沸腾的节日。看着太阳在东山顶上露脸,就开始净场、拆垛、铺麦、套牲口、安碌碡,经过麦垛里十多年的二次成熟,新麦更加成熟饱满,香味也更加沉实内敛。一天时间,太阳绕着山畔转,树影绕着太阳转,碌碡绕着麦场转,翻过三遍,又碾过三遍,开始刮尖、起场,等到场中央堆起一座小山,太阳已经西斜,最火热的晌午即将过去。那时候还流行各家变工,尤其遇到扬场这样的把式活,不是谁都能干得了。扬场需要不大不小的落山风,太大太小或者旋转的风,都不适合扬麦。等风的时候,忙活了一天的人就可以懒散地坐在场畔的树荫下,喝一口豆水汤,抽一根旱烟棒,说天气,聊收成,谋划着秋播的麦种和儿女的婚嫁,话语之间,都是美好的憧憬和务实的打算。庄户人的日子像种庄稼一样,一茬压着一茬,有条不紊,不误农时。
一季庄稼,一季煎熬,所有流过的汗水、出过的力气,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满足而幸福的笑意,深深浅浅地荡漾在庄稼人的嘴角和眉眼之间。庄稼人的日子过得辛苦,却从来不会计较得失成败:丰收了,是老天爷赏饭;遇到灾害减产或者颗粒无收,也是天意,是老天爷不给人饭吃了。只有豁达无争、随遇而安,无论生死疲劳,都能泰然领受,这样才能卑卑服服甘心做一辈子庄稼人。
处暑一过,热浪渐退,秋风渐凉,大地上呈现出斑斓而丰富的色彩:高粱红了脸颊,黄豆干了豆荚,谷子低下了成熟的头颅,玉米挺起饱满的肚腹,一切恰到好处。从芒种到秋分,人们忙碌而欢喜,村庄显得殷实而富足,各种劳动果实次第登场,大场上从早到晚都处于热闹与祥和的状态之中。男人们索性打地铺睡在大场上,与刚刚收获的粮食一起度过凉爽的初秋之夜,畅快的鼾声与清亮的蛙鸣此起彼伏,一唱一和,共同奏响村庄的小夜曲。
麻雀总是一副永远吃不饱的样子,叽叽喳喳,成群结队,从这块地里飞到那块地里,从大坪上飞上山洼间,四处觅食,不知疲倦。邻家大爷生性幽默,说话讨巧,他一边吆喊着驱赶雀群,一边絮絮叨叨跟麻雀说话:“雀,雀,乖得很,吃上些就到别人家地里去吃吧!家里喂着一口过年猪,还等着这点口粮呢!”蹊跷的是,雀群竟然真的飞走了。问之何故,他故作神秘地说:“我懂百鸟言语呢,说话雀儿听哩!”在村庄里,麻雀也天生占着一份口粮的。还有黄牛、毛驴,甚至狗和鸡,庄户人把牲畜叫牲口,有口就有粮么!
冬天伴随着一场刮地风不约而至,大地一片萧索,坚硬的北风似乎要把门前的青石条都要吹酥冻烂了。入夜,飘起大片大片的雪花,油灯昏黄,窗外簌簌有声,很快就进入了沉沉的梦乡。早晨的鸡鸣显得粘稠和凝重,仿佛嗓子里含着一块浓痰,抽了一辈子旱烟的外公的嗓子在早晨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起来推门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覆盖了整个村庄和大地,也掩盖了村路与人迹,模糊了天与地的分界线,人间一派混沌。家家窑口屋顶处的炊烟,依然照常袅袅升起,聚散离合,缱绻勾扯,化作一层薄薄的青岚,笼罩在雪野之上,缠绵在庄院之间。庄户人开始享受一年中最安逸的寒冬腊月了。

石波 摄
铺着席子的土炕在干牛粪的烘烤下热到烫屁股的程度,男人们的头都要睡扁了,翻个身继续呼呼大睡,仿佛要把一年的疲累都烙透散尽。晌午睡起来再咥一大老碗干调面,打个饱嗝,抽支旱烟,日子只能用两个字形容:舒坦!女人们有做不完的活计,忙罢三餐茶饭,安顿的狗进了窝、鸡上了架,炕洞里重新煨了柴火和牛粪,这才脱鞋上炕,忙着打袼褙、纳鞋底,要给男人做几双千层底的布鞋,要给老人和娃娃做一双棉窝窝。俗话说,女人的脸,贴在男人脚面上。在村庄,一双鞋子看的是女人的针线茶饭手艺,也看的是一家人日子的美满和谐。
过了腊八就是年,家家户户忙着杀过年猪,磨豆腐,灌灌肠,起面蒸馍炸油货,豆豉、黄酒都是提前务弄好的。一个腊月,村庄里弥漫着饭菜美食的爨味儿。有钱没钱,盼着过年,过年是村庄最隆重的节日,不仅在于辞旧迎新,更重要的是庆丰收、敬神灵、祭祖先。神灵是护佑,是心灵上的一份安妥,无论山神、土地、灶奶奶,还是牛王爷、马王爷、水草大王爷,虽然缥缈不可琢磨,但冥冥之中护持着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保佑着一方的风调雨顺和幸福安康,这是天地的法则。祖宗是血脉,是家族精神的寄托,谁若自动割断了亲情的维系,就活成了独户,无论贫穷与富贵,在村庄里都会失却颜面,这是伦理的法则。村庄的人,看似隔墙另门住着,其实都在依照各种法则活着,孰远孰近,孰亲孰疏,在关键时候,比如过年,或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小情的时候,立时就显现出来了。
除夕之夜,整个村庄都进入一种严肃而神圣的氛围之中,布面发黄,图影斑驳,散发着久藏霉变气息的祖先影图徐徐展开悬挂在窑掌,四荤四素、四样面食干果的贡品整齐地摆上八仙桌,香炉、蜡烛、线香、纸表、水酒等一字排开,阖族老少男丁全部到场,焚香,化表,奠酒,三叩九拜,躬身长揖以毕,全部祭祀程序才算完成。裹着小脚的奶奶等这些庄重而肃穆的祭祀敬献仪式都完成了,才会走到大门口,跪下来用木棍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再在圆圈里写一个“十”字,然后点燃纸表,对着漆黑的夜空默默呼唤:“爹,拾钱来!妈,拾钱来!”一遍一遍,如同诵经。果然就生了风,吹着火焰在她苍老的脸颊上舔舐,纸表化作灰蝴蝶,在头顶上盘旋,仿佛奶奶去世多年的父母真的来到了身边。除夕坐夜,初一出新,登门给家家户户的长辈拜年,村路上见面相互作揖问候,走到处皆是亲情的团圆和美食的饕餮,老人们则会一脸满足地说一句:“不成想又多活了一年!”。
过年是旧的结束,更是新的开始。一年一年,大地上不断变换的是时间和人序,永恒不变的,却是草木的荣衰和生命的轮回。
几十年走着走着,村庄里很多人就走散了、走丢了,当然也增加了许多新鲜的面孔和稚嫩的声音。父亲和母亲是最后搬离老庄的人,仅仅三年时间,一棵新生的梧桐树冠已经高过窑洞顶了,老院子里蒿草比肩。再看周边,满眼是倾颓的门楼、坍塌的墙垣,废弃在角落里的苔斑如钱的石磨,依然安在窑肩上却已朽枿不堪的门窗,老庄整个荒芜了。荒芜的村庄也将许多往事和旧梦湮灭了。当然,我不是感叹村庄的荒芜,因为新的居落已经在开阔的田野上又生长起来了,这就是自然的力量。
原来大地深处,一直匍匐着无数顽强的生命和洪荒的力量,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人争夺着生活空间,比如那些走兽和飞禽,比如那些根系强大的野草和亭亭华盖的老树,还有每日奔走不息的蚂蚁,和那些已经被我忘记了名字的昆虫。村庄一直拥挤和热闹着,从来就不曾寂寞过。
而让我唏嘘感慨的则是,曾经不堪其苦,拼尽浑身气力也要逃离的村庄,如今却成了回不去的故乡;在外漂泊的游子转眼成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当我有力气在土地上劳作的时候,我毅然选择了离开;而当我想要回到土地上劳作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了!